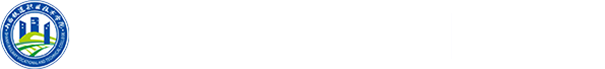(作者:张峰,男,造纸8601,运城临猗人,现供职于临猗县市场监管局,常用网名云梦居士、静庐主人)
晚间从书架上找书读,却发现去年父亲种的几个手捻葫芦,因不会打理,表皮上生出了斑斑驳驳的霉点,于是从百度上学习了些补救的办法,便取下来在水中煮,以便去皮后盘玩。在煮的过程中,竟然满室生香,其味让人回想起小时候的一幕情境:暑假从地里帮大人干活回来,干渴难耐,从凉水瓮里抓起浮在水面上的葫芦瓢,舀一瓢凉水咕咚咚灌下,就应了当前的一句网红语: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那水瓮里的凉水,因为长时间浸泡葫芦瓢的缘故,葫芦的木质清香弥漫其中,掀起瓮盖,香气扑鼻而来,让人觉得生活的美好。而此时,微信群里晓兵弟正好发来“品味人生”的视频,是啊,人生该当知味,知而后品,斯乐可为。
五十年的人生,在这葫芦发出的香气里云蒸雾绕了一番,我顺手从中抽取了几种味道出来,化作了如下自谑式的文字,又因为缘起于葫芦之味,故以《葫芦况味》为题云云——
人生之初,混沌蒙昧,吃了就睡,近乎于神,其时之味,已被造物者收走,不可寻得,或是半个世纪的世味熏蒸,染污太重而不得知的缘故吧,奈何奈何!而后渐次有了意识,人生之味接踵而至,伴这色身沉沦至今——
孩童时傻傻呆呆,但能得温饱,即可酣然入梦,与猫狗无异吧。我记忆里的童年,就有饼干的味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声浪还在此起彼伏,我的记忆里竟然找不到斗与批的影子,大概那从大城市里发出的骇人的声浪,一路呼啸,到了农村,就声疲力竭了吧。只记得那时总是缺吃少穿,少穿好说,冬天冻坏了,春天就好了,缺吃真是难捱,粮食不够就拿菜补,白菜萝卜南瓜红薯做成各种吃的,佐料是最便宜的盐和酱油,一年到头的清汤寡水,嘴里能淡出个鸟来。我不是个好吃手,又不像其他小孩子一样闹着要吃,让大人们为难发愁,饭难吃就不吃了,常常饿得吐酸水,瘦骨嶙峋的,顶着个大脑袋在巷子里晃来晃去,大人们就心疼,我的曾祖母和我的外婆就都对我存着偏心眼儿,时常藏了好吃的给我。那时所谓的好吃的,是糖果点心之类的零食,我的曾祖母就曾把一块不知藏了多久的干点心给我,我费了好大的劲都咬不动,那是我有生以来咬过的最硬的点心。
我总记得巷子里一位上了年岁常年抱病的奶奶(她和我的祖母关系极好,而我的祖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是因为她的饼干。她身体不好不能下地干活,就时常孤零零地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忙忙碌碌的人们从她面前走过。晚辈们逢年过节看她时送她的饼干,她总是舍不得吃,时常拿出几块装在口袋里,给巷子里过往的小孩子们吃。我在她家门口晃悠时,她就赶紧叫住我,把捂热的饼干悄悄塞到我的手里。我大概总吃过她给我的几十片饼干吧,从那时起,饼干的味道就深深刻在我的生命记忆里了,酥脆香甜,满口留香啊,一片饼干就足可安慰我因饥饿而吐酸水的所有的难过。那位奶奶后来活到了八十多岁,我只要回村里,总要从她家门前过,已不再是为了吃她的饼干,只是觉得心里亲,想陪陪她,和她说说话,虽然她后来已经有些糊涂,会记不得我是谁。老人去世时我专门赶了回去,在她的灵前磕了头,并泪眼模糊地忆起她老人家塞到我手中的温热的饼干,以及后来再也吃不出来的香甜滋味。
小孩子,有谁不是吃货呢,大人们的世界太过遥远,理想信念什么的更谈不上,大人们顾不上管,还轮不上老师管,小动物一样乱窜,大伙都是穷人,穷人总在折腾吃饭的事,所以能动心的味道,就都在嘴上。
如果人可以不长大,我到宁愿停留在那份简单的纯净里,但这无异于痴人说梦。退而求其次吧,像那个叫做丁真的网红少年也好,甘愿留在家乡做个有文化的牧马汉子,就连华春莹大姐都对他艳羡不已。他的家乡在理塘,理塘,蓝蓝的天空,辽阔的草原,多美的地方,那里也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乡,仓央嘉措就没有丁真这么幸运,他顶着光环离开了美丽的理塘,却戴着枷锁走进了苦涩的青海湖!
命运之手总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于是,人生诸味不请自来,由简而繁由嘴而心,交替变换,混杂翻滚成一锅热气腾腾的熬菜(家乡一种荤素乱搭佐料丰富大锅慢火炖煮而熟后泼上油泼辣子的吃食)。
管他呢,趁热咥上一大碗,你看,人生海海,就有了演不完的悲喜交加。
少年时的味道,比孩童时多了些。
比如课本的味道。上了学,就有了课本,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可能是印刷的问题吧,都有很重的油墨味,刚发的新书,打开闻闻,会打喷嚏,我喜欢闻书本的味儿,倒不是因为书本里的知识,完全出于好奇。课本的纸张质量也差,有些糟,经常是还没到学期末,书就从中间断开了,32K变成了64K,一本变成了两本,拼起来才能看,还会因为书烂了挨老师和家长的骂。尤其是冬天,清鼻涕和小手冻疮里流出来的血水粘在书页上,脏兮兮的,还掉渣,让人担惊受怕的,但即便很爱惜,包的严严实实也是没有用的,该烂的时候它还是要烂的,老师还是会骂我们手上长刺的。
再比如猪圈和猪草的味道。那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一是可以卖钱补贴家用(我的两周岁照,就是父亲用卖了猪仔的钱在镇上的照相馆照的),二是逢年过节杀掉改善伙食,三是家里有个红白喜事的,就指望自家的猪上席面了,四是猪粪是庄稼地的宝,每年都要出好多次圈(出圈就是把圈里的猪粪挖出去,再往圈里垫上新土,挖出去的猪粪要集成堆等待发酵,发酵好后再拉到庄稼地里做肥料,周而往复)。我家的猪圈在大门外,常年能听见猪哼哼,猪认得我,更喜欢我用树枝给它挠痒痒,更能常年闻到猪圈里的猪屎尿味儿,尤其是夏天,那味儿更是刺鼻呛人,人们都习惯了那种味道,似乎并不觉得臭。那时候,人都没多少吃的,何况猪,主要的猪饲料就是地里的青草,还有红薯蔓萝卜缨等,红薯只有等到冬天才从窖里吊上来蒸熟了喂猪。少年的我,自然而然就成了割猪草的主要劳力,每天一放学就挎上篮子拿上镰刀去地里割草。割得少,怕猪不够吃,也怕大人骂,割得多,怕我背不动,时常和小伙伴们相帮着抬回来。还得摸清猪对草的喜好,那些草喜欢吃,那些草不喜欢吃,那些草压根就不吃,都得门儿清,草味儿很好闻,温柔地包裹起少年的心。我家没养过大牲畜,记得我上初中时总厌学,一次父亲到学校找我,说不想上学就不上了,到集上买头牛或者买头驴,回家种地算了,我那时瘦小瘦小的,就有些害怕了,暗暗加了把力,初中毕业后考到了省城的小中专里,也从此跳出了农门。
再比如煤油灯的味道。我上小学时,学校不通电,冬天昼短夜长,早晚天黑,早读和晚自习就靠各自的煤油灯来照明。我的煤油灯是父亲做的,用旧墨水瓶做灯座,用自行车的废气门做芯管,用妈妈纺的棉线做灯芯,灯油用的是煤油,冒着黑烟,鼻孔总是熏得黑黑的,吐出的唾沫都是黑的。我家离学校远,冬天捧着煤油灯去学校,怕煤油撒出来,小心翼翼的,到校时经常手就冻破了,裂开好多道口子,破口处不流血,流清水,没破口的地方肿肿胀胀的,像发酵了的面团,明晃晃的,晚上回家后在炉子上烤,又痒又痛,难受极了,就这样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天气暖和起来了,手上的破口才会发痒结痂,慢慢好起来。
少年的味道,有一些些苦涩吧。不过那时的苦,倒也不见得有多苦,大家都那样,苦中作乐,相互取笑着,苦味里还有着丝丝的甜,那是少年人一起抱团儿发出来的甜。发小,那一群天真的少年人,是我一辈子的“回甘”。
微信群里和几位好朋友聊了会,顿觉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又喝了会茶,老白茶浓郁的草木味道让人着迷。想要接着写时,竟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告别少年后,发觉真正苦涩的味道来了,决然不是当下老白茶滑爽柔和的味道了。人生真正的苦涩,是从少年离家后开始的吧。生活倒是渐渐好起来了,已不再为物质贫乏而发愁,而我原本就是一个对物质需求不大的人吧,但一路走来,却为何总是困惑连连忧苦不断呢?
我从最后的农耕社会里走了出来,走到了灯火通明的大城市里,走进了机声隆隆的大工业时代,又走到了琳琅满目的大市场里,走进了熙熙攘攘的赶潮人群里,风风火火的,又懵懵懂懂的,其间滋味,又何止酸甜苦辣咸这些舌尖可知可品之味。一些味道,可知不可品,一些味道,说不上来却总想品品,一些味道,一品就变了味儿,一些味道,越品越不是味儿……
被命运之手抚摸过的人生,其中况味,岂是刺鼻呛人那般简单,打破了五味瓶,搅成了糊涂粥吧。雪芹同学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辛酸泪是啥味儿?且留待后来再说吧。
有些虎头蛇尾了,这也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人生之味,总是有说不上来的时候,当下即是,可能是未发酵好的缘故吧。譬如刚出圈的猪粪,是粪不是肥,比喻得牵强些,却也差不离吧。米兰•昆德拉说,粪便是比罪恶还尖锐的神学问题,好吧,离神远点,还是回到葫芦上来吧。
葫芦,是要自然成熟的,不能急着摘下来,不成熟的葫芦还没有完全木质化,皮肉都是嫩的,经不起风薅日晒的,一旦离了蔓儿,太阳底下热气一蒸,就蔫了,蔫成一副丑陋不堪的样子,又瘪又塌,抽抽扭扭的,让人看着心乱,直接成为美学命题,这样的画风突变,让味道情何以堪!
涉世前的那段岁月,虽然懵懵懂懂,却也干干净净,虽然有些遥远,却更值得回味,心无挂碍的单纯,以及满心眼里的天真,就是一片未曾染污的世界,谁又不是从那个世界里来的呢!而我这些年匆匆赶路,竟顾不上好好回头看一上眼,昏聩颟顸,像个没心没肺的浪子。
东坡居士绝对算得上是个知味之人,更是个笑嘻嘻的打不倒的小强呀,人生种种际遇与艰难困苦,不过是多识了几种味道,算是赚了。嚼得菜根烂,品得猪肉香,端起酒杯向故人,一笑千古成佳话: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后来人纷纷拾其牙慧。北京有着大院子的冯唐就说,尚未佩妥剑,转眼便江湖。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
只是说说罢了,出走多年的我,归来时,可还是那个傻乎乎的少年?
我想到了一种味道,——禅味。何为禅味?不可说不可说也!
你看那葫芦,你摇它,就听见它肚子里呼呼啦啦地响,但它就是不开口,一开口,葫芦就碎了呀。
虽说人生苦短,前路依然漫漫。我听见许多年前的那个少年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