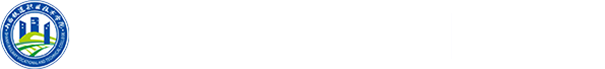相信命
作者:笼中善哉
2018.6.8
班级:统计8401
题记——捡几粒芝麻,努力榨出点油星星。
故弄玄虚起了个唯心主义的题目,诙谐一笑“呵呵,呵呵。”起身,自己拍了拍屁股,细细想来生活原本就是这样,芸芸众生都在努力为嘴唇抹点油,为面子争点光。
来到这个世已经鬼混了五十多年,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历了坎坎坷坷的事,细梳理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一个人的一生就像神仙随意抛起的一块顽石划过天空落在了该落的地方。
(一)
童年的记忆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隐隐约约中和姥爷一墙之隔的蒋家大院里死了人,大人们忙忙碌碌出来进去,一群流着鼻涕的孩子(记忆中那时的孩子都很邋遢)跟着看热闹。
“烧纸……”
“叩头……”
“起丧……”
这是童年最早的记忆。多年后,小山村里死了一茬又一茬,有少年夭折的,有八九十岁寿终正寝的,扳着指头数数忘记的不少,记住的也不太多,倒是把生老病死看淡了许多,细想生活就像掐指一算去年落了几场雨,刮了多少风,记住的又能有几。
那个年代还没有通电,外面的世界就在大山之外,某一天五六个瞎子(盲人宣传队),一手柱着棍子,一手托着前一个人的肩膀,像一条绳上的蚂蚱进了村,晚上安排一家一户吃饭,记忆中牵着老瞎回家吃过饭。
点起马灯围在官房院听老瞎说书。
“妹妹啊吃黏糕,哥哥我肚子咕咕叫,有心让妹妹装在裤裆给哥带出块,又怕粘了妹妹的毛……”
多年后,一墙之隔的左权县盲人宣传队唱出了名堂,唱到了人民大会堂,唱响了全中国,而和顺的盲人宣传队顺应时代潮流包产到户,各人忙各人的,东家出来西家进,要几个零花钱(不过听人说收入还相当可观,但愿)。
有句流行的诗歌唱到:“外面的世界多精彩……”,童年时总是想走出大山看一看,看一看山那边落下的一条龙,总是想到县城的路不要走那么远。
(二)
隐隐约约记得当时过了正月二十就要开学了,七岁的我第一天端坐在官房院的北房教室里准备念书了,也只念了三五天就再也不想去了,老师叫也不去,母亲送也不去,逼的没办法,由本家年纪大一点的哥哥每天领着三四个同学,从家里逮住抬到教室,谁知一转眼就逃出教室躲得无影无踪,一连几天母亲也没办法,到后来只能随了我,像野地里的小草自生自灭不去就不去吧。
年纪相仿的都上学了,母亲要上地劳动,只留我一个人躲着学校后的在山坡上,土堆边玩耍,一会儿逮蚂蚁,一会儿捉蚂蚱……
九岁的后半年,突然有一天对母亲说我要去学校。谢天谢地,母亲亲自用劳动布缝了个书包挎在我的肩上送我到了学校,我对母亲说送我三次,确切的说送了一次就自己去了,就这样一年级后半年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只是可惜了那一个新书包,第一天上学回家,把书包扔到火炉上烧了个大窟窿寿终正寝。
也许是年龄大的缘故,理解能力强,小学念了四年半,数学就没费多大的劲儿,回回考试100分,“羊群里涉出的狼”成了17岁女老师的得意门生。
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学区内的学校所有学生要去参加做操比赛和数学竞赛,走在半路上又逃跑了。老师特意回来在村后的羊圈里逮住扭着到学区参加数学比赛,不巧又争气得了第一名。
上到三年级我们换了教室,教室后面有个窗户,男同学懒得外出尿尿,都站在窗台上向外尿,比赛着看谁尿的高,尿的远,一次我正在方便,老师站在我的身后喊:“下来!”
射出去的箭也没办法收回,只能红着脸尿完,记得那一次挨了重重的一教鞭。
三年说过就过了,我的老师调到外村教书了,那个时候有个同学的父亲在煤矿当工人,从他家里拿了一条白毛巾(记忆中好像最小的的那一种)我们每个同学(三个)每人出了两毛钱共六毛钱,这是人生开始第一次送礼,送给我的老师心甘情愿。
仅仅是个开始,想不到五十年来每做一件事都和送礼分不开,我的国我的这个人情的社会,这个有“礼”(理)的社会。
又来了个男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姐夫,参加工作后每每和姐夫说起拿木棍体罚我们,我的同学几个密谋了好几次,计划在晚上睡觉时,对着窗户扔一块大石头,可惜一直没有实现。有次坐在一起吃饭说起来,姐夫哈哈笑一笑,“还有那事?不记得了。”
(三)
离我们村二里地的国营南窑煤矿(现如今迁到我们村后半死不活,改制后已经停产了好几年)买下了第一台12英寸黑白小电视,附近村庄的大人小孩晚上七点多聚在一起观看,黑压压一片。印象中有《高山上的一根草》、《七品芝麻官》、用现在的话火了的还有《加里森敢死队》,那一段时间人手一把用锯条磨制的小刀,同学打架都亮出家伙,细想83年严打或许和这部连续剧有关,谁能说的清楚。
近五年的小学生涯说过就过了,小学毕业上初中要到三里外的南窑学区上学。前一段时间还去了一次南窑村,学校还在只是破败了许多,教改学校取消了,村里的孩子都去县城上学了,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留守在村老人去世,几百年的村庄也就落下了帷幕。
当时我们有两个老师,教数学的女老师是亲戚(她的儿子和我是同学,现在我们都在小城里居住,没事的时候常在一起吃个饭),一个是高中刚毕业的男老师教语文,年纪也不比我们大几岁。
上初中后,对于学习远不像现如今的孩子起早贪黑人人戴个小眼镜人接人送,我们倒像散养的马驹家里不闻不问自由蹦跶。当时男女同学不说话,
男同学一贯欺负女同学,有几个同学因此退了学。
男同学挨打是家常便饭,教鞭棍都打断几根,学越来越懒得上,三五成群结对逃学,早上背着书包从家里出来,到离学校五里的油库看电视,或者到七八里的食品公司猪场看杀猪,晚上回来在陶瓷厂偷花盆和尿盆,多年后在老家的屋后还能翻出一两个。
十三四的男孩子,嘴唇上已经长了虚毛,有几次几个同学合计逮住一个同学脱了裤,看看裤裆里还多了些什么没有,这样一轮下来谁也逃不掉。
经常这样逃课也不是个事,半年后数学老师和我母亲说像我这样混下去就黄了,不如下城上学,正好那一年全县从小学毕业生中招100名学生到县城上初中,数学老师托关系让我又重新参加了一次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有幸考在了100名以内。
(四)
那么咱就再说说在城里初中(和顺二中)那点事,没上过一中,作为和顺山区小县的一个“读书人”(捂着嘴偷偷乐一下,晋中有一个著名作家在微信群里看了我的作品夸奖说:*秀才好,还点了一个大大的赞。我点了一个呲牙回复,写到谢谢老师,承蒙夸奖劈柴的“柴”)是一生最大的遗憾,不过上了和顺二中也能够够炫耀一阵子,毕竟当时15个乡镇都设立中学,毕竟多数人上不了二中,毕竟那一年全县从小学毕业生中招了前100名,名次单数135…和双数248…分了两个重点班,一个在一中,一个在二中,毕竟那一年有我。
进城了,暂时成了重点班的重点人,美哉!悠哉!用我们班班主任的话说,只要好好学习用到功,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市民大队的门口,再努努力考上个学校,就能脱离农村分配工作吃上皇粮,做一个公家的人。
说归说,当时也没有那么多想法,日出而学,日落而息,放假后回村和母亲一起锄地割谷,不过劳动也是做做样,一来母亲怕我累着(母亲一直说我身体不好,直到前几年母亲卧床不起还私下说我身体不好少做点家务活),二来我吃不得农村那个苦。
多年参加工作后有几次回村里,几个本家的大娘大婶见了我还说,还在县城上班?当官了?听说你当官了,当了个什么锅长(股长),比咱村书记G**的官还大。还在财政局?昂——财政局是个好单位,有钱,是不是家里都堆满了钱!听说你住上楼房了,还是人家财政局的干部,从小就看出是个中用的人方盘大脸的。以至我私下用镜子照了照又黑又瘦,自认为没有一点福相,不过眉眼还算周正。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代代红中学那一年刚刚改成和顺二中,1981年我哥代代红中学高中毕业,也就是那一年已经恢复了高考制度三四年,只可惜偌大个中学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包括中专师范)。
哥骑着自行车把我送进二中安顿下走了,宿舍是一个教室改成的大通铺住了二十几个同学。
先说说吃的事,住校生由父母把玉米拉到乡镇粮站兑换成山西粮票然后交到学校,我们每个人每天三毛伙食费,每月交9块钱就可以拿着大碗去学校食堂打饭吃,不管饱一人一份,当时的记忆就是一个“饿”,多年后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咸淡都能入口,从来不挑肥拣瘦(更何况参加工作后多数是白吃白喝)。
早晨一大碗散面粥,如果食堂有剩下,听大师傅敲锅还能再打半碗,多年后还留有阴影不能听别人敲锅,敲脸盆都不行,一听脸皮就发烧,感觉自己像一个讨吃的,我自知脸皮虽黑但不太厚。当时住校生那个能吃,两大碗都不饱(到现在一小碗都吃不了),现在的孩子都想不到。就那样即便两大碗也挪不到中午,每天上午11点的时候肚子饿的咕咕叫。
吃的事情一直挨到冬天就会好一点,回家带上母亲用小口袋装的小米,晚自学后回宿舍用铝饭盒煮点小米粥,几个同学把肚子再填补一下。
有次煮粥,我坐了个三条腿板凳挨着火炉洗脚,一不留神大腿滑在了炉上,烧伤了一大片,幸亏那一次烧伤的是大腿外侧,没泄了元气,烧伤后好几天裤都不能穿,只能躺在通铺上睡大觉。
再说说住的事情,二十几人睡着一个大通铺,晚上咬牙的,打鼾的,还有说梦话的,好在当时年龄小,跌倒就和死了一般呼呼入睡。
只是早晨起来没办法洗脸,说不定哪个同学夜里把尿撒了一盆,没办法吵骂一阵,只好自己端出去倒了,洗一洗再用。
打架的事是常有的,躺在床上瞎叨舌,几句话说不在一起,重新穿上衣服两个人干一架,然后躺倒再睡,第二天醒来早忘了个干净,称兄道弟急急忙忙穿起衣裤一起到操场跑操。
有一年冬天,我们用棍子故意将黑板撬松,然后报告给总务科的老师,学校派人把黑板拆除。晚上,一个同学用火柱从砖缝通了个眼,墙的对面是女生宿舍也住着十几个女同学,胆子大一点的偷偷向那边望,至于看见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吗就不说了。只过了一个多星期不知谁掏了一块砖,露出拳头大个洞,好几天那边的女生都只好穿着衣服睡觉。
“男生和女生透了气!”总务科的一个女老师说。随后派人用泥堵死,宿舍才又安稳下来,一直到初中毕业。
学习的事情就不多说了。 初一的时候当了短暂的一个学期班长,也就是学生时代最大的官,管着五十多个同学,不过生就不是当“官”的料,不能做为班主任的喉舌给老师通风报信,那一个学期“协助”同学哄骗老师,特别是哄骗班主任,包庇同学,不能帮助同学改正学习中的错误。到第二个学期一开学,我们班召开“民主选举”,选举新一轮班长,落选是注定的,可惜没见选票,只是班主任宣布某某同学以某某票全票当选,以至于多年后对此事耿耿于怀。
初中毕业考试前,我报的志愿是榆次一中,学校教导处主任(原物理老师)说榆次一中不招人,就改成了中专,那一年有史以来和顺二中初中毕业生整体成绩高于和顺一中,前十名占了六名,第一名是我们班的,第二名就不说谁了也是二中的。
初中三年就这样不紧不慢结束了,后来上了中专,再后来参加了工作,多年后想想我的读书生涯也就那么短短的吊儿郎当几个年头。
如今碌碌无为走过了大半辈子,吃穿到不是大问题,经常缺钱是真的,到如今还欠着同学十万没有还。经历过的事太多,相信了人生每一次的落脚都是命运的安排。
生活啊,谁能说的清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根。
等一等,请再等一等,在恰当的时候,一不留神一句话或许就能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轨迹,也许这就是命运,好像冥冥之中命运早就安排了每个人的归宿,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
写了这么多,没有写出的还很多,最后用我的真心话出自肺腑,感谢生命中与我相遇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小学和初中的所有老师,还有我的所有同学。